【散文随笔】陈秋旋:与江为邻
散文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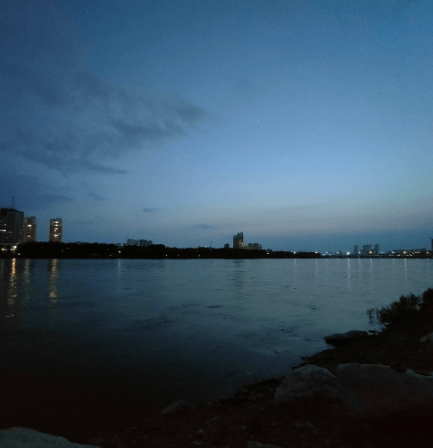
夜来风起,忽起了访水的冲动。
十年过去,与异域的朋友偶然聊起,才猛然察觉家距长江码头不过一公里多。于是夜班归家的路上直接调转自行车头,向人迹更清冷处驶去。
码头前是一座水泥筑就的桥。宽而厚重,坡度极高,相较于古诗里小巧玲珑的同类,更像是“关山难越”。这桥位于秋浦河尽头,它正于此处汇入长江。秋已过半,桥的另一端悉数隐入白浓浓的雾气里。若是在桥这头的热闹处,这雾便海市蜃楼似的远,好像人一讲话、一做饭,就把这雾气喷散了。可眼下,我越是艰难地踩着踏板向雾气深处行进,它就越是沉沉地将我罩住。
夏季汛期,河岸上会亮起一闪一现的红色灯塔,这会儿却已歇息。我多么盼望一座余光中诗里“无畏”的灯塔啊!狠狠一拳,击退“那一片恫黑”。
此时树叶尚未黄落,正是最为寒翠的时节。我费力地蹬行,带起一片呜呜的风声,身上两件衬衫愈发缩得紧了。终于路灯也不得不退场。周遭的房屋树木一片模糊,间或向江际延伸出一二分叉的小道。所幸一路平坦,我仍可攥紧了车把抬头挺胸。我从不信什么魑魅魍魉之说,然而雾气森白一团,隔着加绒长裤,湿沉沉地舐过我膝盖下前几日摔出的大片创口,竟像是实物一般。
码头黑漆漆的铁栅栏是牢牢锁上的。我跳下车,攀着栅栏奋力眺望,仍不见一丝涟漪。江浪渐渐敛起锋芒的秋日,更听不见东坡词里的所谓江声。但一江之水就横在那里,并不因我看不见它,就与我的心同归于寂。
母亲说,江这边是池州,江对面是安庆。
由于我的各类证件上一直保留着外祖母一脉渡江而来的少数民族身份,我打心眼里认定,安庆乃是我真正的祖籍。童年时期,我多次随着大人去往安庆不同的亲戚家做客。直到今夏,我赴赣与好友小聚。周转途中,我才第一次用成年后的眼睛,如此认真地打量着它。
安庆站外,我挑了一束由红、橘、粉、白各色组成的盛放的玫瑰和一束蓝蝴蝶似的满天星。我将前者献到城郊的陈独秀先生墓前,玫瑰敬德赛,浪漫归先驱。后者则留在闹市区附近的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门口,取的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之意。
展开全文
一段可歌可泣的近代史,一个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安庆,因此从长江裙裾边的一座水墨小城,变成了国人心中夕阳胜血的英雄故里。一江之隔的我,也由衷地为之自豪与落泪。当我走进花店里挑选鲜花的时候,我不由得用一种亲切的、热烈的语气说道:“我买花是去看望以前的老乡呢!”
我行走在市中心逼真的古城,怀抱满载敬仰的花束,好似穿梭在时间的迷宫。午后的阳光斜斜飞过马头墙弯弯的檐角,打在花瓣滚落的粒粒水珠上,折射着人类历史中来之不易的片刻宁静。蓦地,我抬起头,面前素墙上的大楷竟不是桐城派的之乎者也、文法唐宋,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诗人海子一首并不出名的《给安庆》: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二十世纪末频发的“诗人之死”,在文学史投下一团江雾般的谜。我们至今仍然不知这位早逝的天之骄子,是怀着何种心情,在一个尚未老到乡愁袭身的年纪,为故乡写下了这首扑朔迷离的短诗。只是这一刻,至少我相信,在一次又一次往返于长江两岸的时候,我亦曾一次又一次面朝着江水,什么也不说,静静地张望着。彼时的我,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携着这段自江对岸遥遥采来的遐想,我跨上自行车,转身离去。江水从不因我看不见它就停止流动。桥上白亮亮的路灯下,雾浓而醇。整座城中的雾,皆由江里的水汽凝成。
我深吸一口,江水顷刻凉入五腑。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在阳光最酽时再度造访长江。
翻越水泥大桥实在太过费力,我的后背冒出一层薄薄的热汗。风冷刺刺地擦过脸颊,阳光却有点烫人,有点眩目。此处原是水文单位的旧址,楼前的荒地现已改作驾校的训练场地之一。房屋本身未经修整,老式的深蓝玻璃灰扑扑地暗在那里,瓷砖外墙半泛着黄。
这一回,码头大敞。漆有黑色数字的水位观测塔最先映入眼帘。江水很静,灰中透蓝,被阳光蒸出一股温热的水腥气。我上颚一紧,几欲作呕,可嗅着嗅着,它竟化为另一股无形的江水,在我的鼻腔内缓缓涌动。
倏然之间,响起一阵长而嘹亮的鸣笛。我循声而望,更远处,粼粼水光之间,一艘轮船整装待发。甲板上的电动车、摩托车一辆套着一辆,不余一丝空隙。转回身,离我更近的一侧,芦花丛灰灰白白,疏疏密密,承袭着国画里勾皴擦点的笔触。底下半隐着一撇废弃的木制渔船,船尖立着一竖窄窄的白颈乌鸦。
对岸群木时已尽凋,更显天穹辽远。一点白鹭贴着江堤,时上时下,宛如拨弄着一根笔直的琴弦。偶尔落入水中,留下一圈余音似的波纹。
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宝山,独自寻找1937年淞沪会战中日寇的登陆点。那天,我也曾登上过一艘民用轮船,它同样是被乘客与随行车辆所填满。
昔年浸透烈士鲜血的黄浦江水,今日再也窥不出一点血雨腥风的影子。我向身旁的乘客打听轮渡的停靠点。一位浓眉宽颌的中年大叔起先用上海话热情地指路,岂料换来我的一脸茫然。得知我是安徽南边来的游客后,他立刻换上一口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哦,那我们是老乡呢!”
他们一家从扬州来宝山做汽车配件的生意,因而,我们也算是“共饮长江水”的江南老乡。他和妻子育有三个女儿,一个工作几年,一个大学毕业后退伍不久,一个还在读高二。我与他的二女儿一般年纪。为了解决小女儿读书的户籍问题,妻子带她回了老家。
“生活,不就跟这江里的水一样嘛,顺着流就行。过得好也不用太高兴,哪天过得不好了,也不用太失落!”
他格外爱笑。笑容活像舷窗外的阳光,自眼角一路碎金子似地,撒了个满船。说东道西,漫漫洋洋,从当年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一直讲到眼下陆家嘴前所未有的繁荣。此次带着摩托前往浦东,就是为了完成一单送货。
“这吴淞口,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长江尾’呢。”大叔笑吟吟地背起长江上流传千年的民谣。
抵达宝山前,我一心想要亲眼见证,郭汝瑰将军信里的“如有波涛如山,那便是我来看你了”。然而船至江心,临近入海的江水一波又一波拍打着礁石,不疾不徐,恍若江岸上任何一位按部就班、温和朴实的劳动者。
想来波涛如山的怒状诚然罕见,才会被视为心有灵犀的凭据。倘若先烈泉下有知,可否能再借这一江浪潮,与这太平盛世应和一二?
大叔告诉我,吴淞口的轮渡来回仅有一站。船上几乎不见游客,乘客都肩负各自的工作需要,间或也有几名推着爱车的骑行爱好者。成群的车辆,令我想起纪录片里赶马、赶羊的北方游牧民族。轮渡是独属于我们长三角人的迁徙。
视线落回眼前阳光辉煌的码头。白底的观测塔上了年头,黑色的水位数字已经有点剥落了。
成年之后,我才从网上一些帖子的“边拐”处得知,池州城里的不少菜农,并非本地居民。而是每日凌晨六七点,从对岸一个隶属于枞阳县,名叫凤凰洲的地方早早赶来。趁着城中大多数人尚未苏醒,分散进入几个大型菜市场,中午再乘船回去。他们至今仍延续着这一生存传统。
初中的地理课曾说过,水运虽慢,受天气和风力影响极大,成本却是所有运输途径里最低的。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不知快于古老的江水多少倍。但是留下这个小小的渡口,不是为了更快地追逐什么,而是不断回望,回望,望向那些似乎总要比时间慢一些的人。
每个靠江吃江的孩子都不陌生。199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特大洪灾,夷平了这里的一切。无数条正值壮年的生命,牺牲在这场与无情自然的战役里。洪水退去的废墟上,我们的父辈再度垒起了白塔与码头。每年夏天,我的手机都会收到市自然资源局有关洪涝灾害的提示短信。我知道,到了那时,在红色灯塔威严的指引下,江水又化作一匹被人类驯服的烈马,于两岸之间尽职尽责地往返。
又是一声汽笛。轮船启航了。仍陆续有人骑入码头。几个孩子蹲在候船的父母脚边,在泥地上专心摆弄着自己的卡片。对岸,白鹭起起伏伏地飞着,飞着,犹如一穿一引,连接起水与陆。
也从那些古老的诗句里飞下,飞下,连接起古与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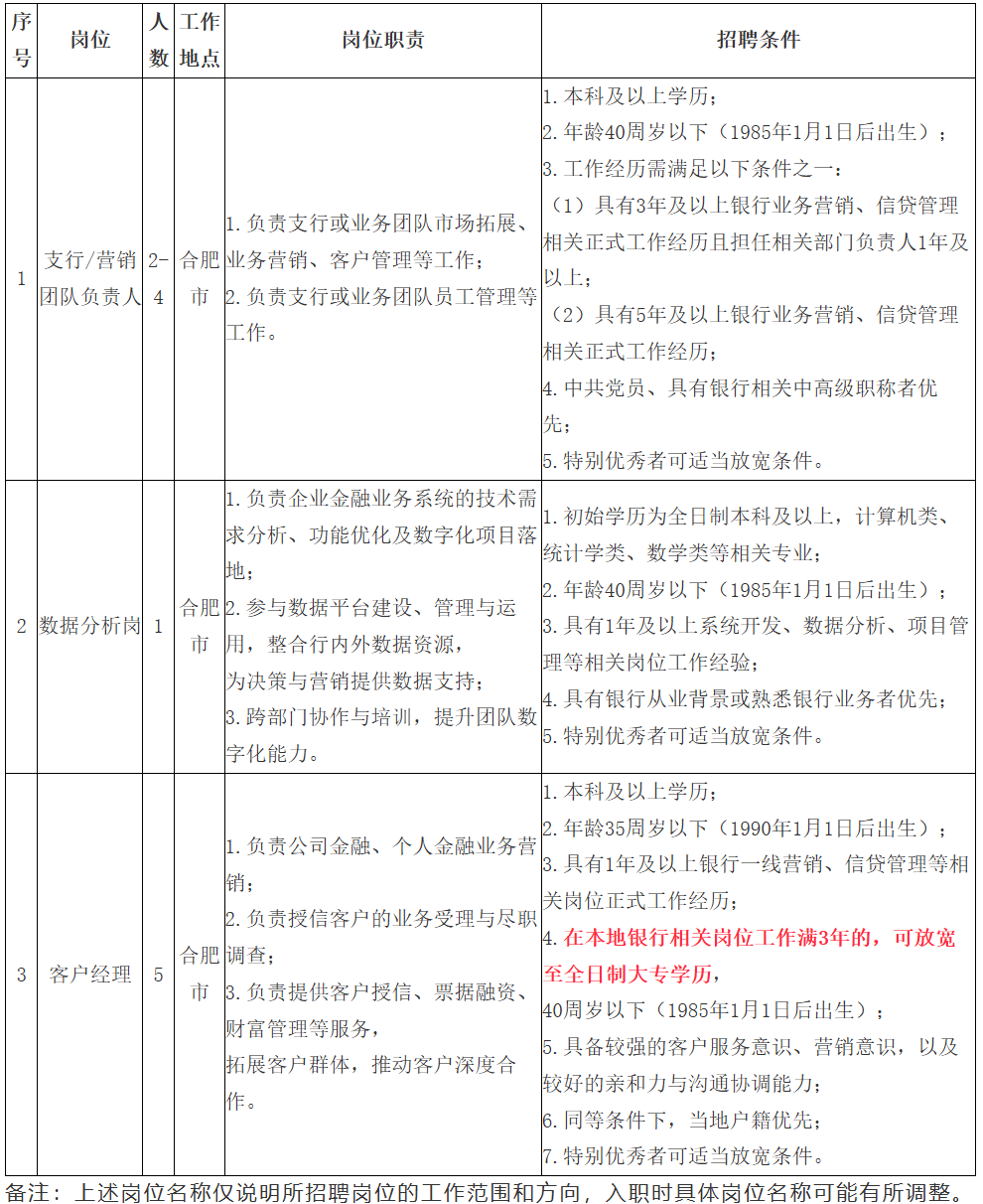






评论